张志伟:《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之“自身”
日期:2025-09-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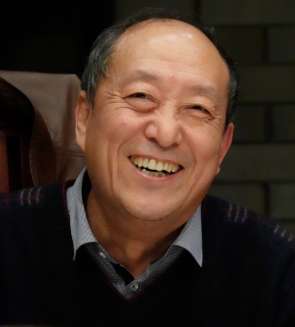
【摘要】《存在与时间》(完成的部分)的导论重提存在问题,第一篇“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描述了此在是如何“从自身跌入自身”而“沉沦”的,第二篇“此在与时间性”寻求让此在“从自身回到自身”而本己地生存的方式,因而此在与其自身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核心问题。我们通过“去存在”、“沉沦”和“将来”这三个关键词,梳理海德格尔是如何通过此在这个个体存在物来解答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分析此在如何能够以“存在”为其“自身”的可能性。
【关键词】存在,此在,自身,去存在,沉沦,将来
此在之“自身”,即通常作为反身代词的“自身”(sich),以及作为指示代词的“自身”(selbst)(亦译作“本身”、“自己”等,本文亦按“自身”理解和解释)等等,虽然只是“小品词”,似乎并不是专门的哲学概念,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出现频率非常高,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准备在哲学上讨论此在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相关的语法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去存在”、“生存”、“领会”、“操心”、“沉沦”、“畏”、“死亡”、“时间性”……等等一系列他称之为“生存论规定”的术语来描述此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活动,这些生存论规定差不多都与此在的“自身”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探究,因为此在这种存在物的“自身”异于任何存在物的自身,通常某物的“自身”指的是某物具有确定的同一性,尽管事物可以是一个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形成过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所实现的自身同一性毕竟是确定的,此在却没有这样的自身同一性。此在为存在所规定,而存在不是存在物,所以此在的自身同一性与存在物的自身同一性不同,体现为全然的“可能性”。
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1]因而“居于”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能够“存在论地存在”,所以存在即此在的自身,或者此在以存在为其自身。问题是,此在(Dasein)作为存在(Sein)在此(da)显现的“境域”,被抛入了可能性的境域,它既可能以存在为其自身也可能不以存在为其自身,或者说更准确地说,此在既可能显现存在也可能遮蔽存在,而且因为存在物的“身份”,此在实际上是以遮蔽存在的方式存在着。不仅如此,当存在通过此在这个存在物而显现的时候,存在就不再是存在自身而“现身”为此在了。此在之自身问题的麻烦即在于此:此在作为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以存在物的方式领会和显现存在,虽然存在“此在化”与存在“物化”是不同的,此即“实际性”(Faktizität)与“事实性”(Tatsächtigkeit)的区别,[2]但是此在之自身毕竟不同于存在之自身。
既然如此,在什么情况下此在以存在为其自身?或者说,存在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通过此在而显现?唯当此在以本己的方式,保持自身为“去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不过,此在“本性”如此,但并非天然如此,此在“天然”逃避自己的存在,它宁愿疏散在存在物之间,混迹于常人世界,逃避自己的存在亦即逃避自身。就此而论,存在虽然是此在的自身,但此在实际上却从来没有把存在看作是自己的自身,这就导致了此在对自身的误解以及对自身存在的逃避,甚或可以说,此即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根源。
看上去《存在与时间》描述了一个此在“从自身跌入自身”(沉沦)到“从自身发现自身”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或者先在的“自身”被此在“遗失”了,然后此在又把它找回来了,并非如此。并没有一个“潜在”而确定的自身有待此在去发现和实现。如果说此在之自身是存在,而存在不是存在物,那么此在如何能够以一种存在物的方式,让并非存在物的存在通过它的存在而显现,就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核心问题。
一、“去存在”:在存在与存在物“之间”
此在之“自身”并非“自身意识”、“自我意识”、主体的自身性等等意义上的“自身”,此在之“自身”与意识、自我或主体无关,仅与“存在”有关。人这种存在物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为存在所规定的,因而此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不是自身意识或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而是如何本己地“去存在”即“生存”的问题。“生存”(Existenz)亦即“站出来去存在”,因而此在“去存在”总是在“出离”自身,“出离”自身看上去就不再是自身,然而此在之自身就是“去存在”,这意味着出离自身就是此在自身——此在是一种始终在出离自身而去存在之中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出离”自身而“去存在”体现了此在的超越性,而这个超越性并非“主体能动性”,而是存在对此在的规定。
海德格尔以“生存”(Existenz)和“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作为此在的“存在论机制”: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而“去存在”只能是这一个此在自己“去存在”,所以此在是一种自己“去存在”的个体存在物。如果我们把存在看作一切存在物的基础和根据,那就意味着存在不是存在物,但一说到存在又总是某个存在物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凭空”跳到存在“之外”去思想存在。我们不要把此在与其自身的存在分离开,此在与其自身的存在乃为一体,不恰当地讲,唯此在“自带存在”,而其他所有的存在物作为现成所予凝固的东西都不可能显现出存在来。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绝不是关于一切存在物的“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产生和形成一切存在物之生生不息的“源泉”。如果按照后期的海德格尔,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称之为“存在”。传统哲学的努力方向是超越个体性而以思想通达最普遍最抽象的存在,海德格尔却把存在问题的解答落实在此在这个个体存在物之上:“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最普遍最空泛的问题,但追问这个问题却也可能把这个问题本己地、最尖锐地个别化于每一此在本身”。[3]
既然如此,此在意识到了它的自身,或如苏格拉底的座右铭“认识自己”,存在问题是不是就圆满解决了?绝非如此。此在之自身不是在意识或思想或理性中被认识的“对象”,而是此在“去存在”的生存活动。由此,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的“知”转向了此在生存论的“行”。人们有时候称之为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不过实践活动仍然有主体与客体的问题,而此在的“行”亦即生存活动须看作此在与其自身的存在“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源始境域,此在之“行”亦即存在的显现。然而,此在之“行”既可能是存在的敞开,也可能是存在的遮蔽,而此在的生存活动恰恰是以遮蔽自身存在的方式“显现”着存在,这就关涉到了此在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在首先和通常并不是以本己的方式“去存在”的,由此就有了本己存在(本真状态)与非本己存在(非本真状态)的区别。如果我们可以把“本己”看作是此在的“自身”,那就意味着此在与其自身是不同一的,然而这也意味着此在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正因为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此在怎么领会自己的存在,它就怎么存在,而此在怎么存在,存在就怎么显现。此在对自己的存在的领会不仅决定着它自己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存在的显现。所以此在与存在之间有着某种“相互需要”的关系:一方面此在因存在而存在,另一方面存在通过此在而显现。所以,此在肩负着让存在显现的“使命”。
然而,此在虽然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物,因而“确实,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仅是切近的,甚或还是最切近的--我们自己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所以,此在特有的存在建构(如果把它领会为属于此在的‘范畴’结构)对此在始终蔽而不露,其根据恰恰就是此在在存在者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离它自己‘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但在前存在论上却并不陌生”。[4]只有此在才谈得上与存在之间的“近”和“远”,一般的存在物根本就不存在远近的问题。此在是因为与存在的关系而被称之为此在的,不过在存在物状态上它是且首先是存在物,就其把自己看作是存在物而言,它不会把自己理解错。实际上,即便是此在把自己看作是不同于任何存在物的“人”,也仍然是一众存在物中的一种存在物,“人”如同物一样是由某种先在的本质(如人性)所规定的,说人有人性仍然是一种物性思维。正是由于在存在物状态上此在离自己最近,它将自己看作是存在物而且仅仅看作是存在物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以至于此在的存在机制始终对它蔽而不露,所以在存在论上离自己最远。不过,即使此在离自己的存在最远,它毕竟是此在,它的生存活动仍然基于对存在的领会从而是存在显现的境域,只不过是以遮蔽的方式而已。换言之,此在在任何存在论“之前”就存在着,此在存在着总有对自己的存在的领会,所以在“前存在论上”并不陌生。
因此,我们可以把此在看作是居于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存在物。存在不是存在物,但存在必须通过某个存在物而显现,不恰当地说,存在在此在这个存在物这里“个体化”出来了,而存在“与此同时”仍然“存在”。这个“之间”并非两个存在物(东西)“之间”,如果我们把存在物看作存在着,那么存在就“不在”,但是在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物这里,存在却又“在此”,或者说,存在就在此在的“去存在”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此在的生存活动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显现,此在可能以本己地显现存在的方式存在,也可能以遮蔽存在的方式存在,海德格尔称前者为“本真状态”,称后者为“非本真状态”。就此在为存在所规定而言,存在是此在的“自身”,但是就存在“个体化”为此在而论,存在似乎也获得了某种“确定性”,虽然此在的“实际性”与存在物的“事实性”不同,但是存在毕竟需要通过此在这一存在物而显现。这就是说,“此在以如下方式存在:它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5]而且以存在者的方式显现存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此在在存在论上的“优势”是以存在物的方式显现存在,套用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关于语言的说明,[6]这既是此在的“荣耀”又是此在的“不幸”:此在能够领会存在,以“去存在”的方式存在,这是它与众不同的“荣耀”,但是当此在以存在物的方式领会存在之时,很可能或者说必然陷入把存在领会为存在物的“不幸”。
所以,当我们说“去存在”构成了此在的“自身”的时候,这并非问题的答案,而是就此而提问。因为此在的“去存在”毕竟也是作为一种存在物的“去存在”,正因为这种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既可能以本己的方式自己去存在,也可能不作为自己地去存在,所以此在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然而此在不作为自己去存在也是因为它能够“去存在”。
如果此在不作为自己去存在,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就是:此在作为谁而去存在?此在是谁?
二、“沉沦”:“从自身脱落到自身”
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颠覆突出体现在他把存在从思想的对象“落实在”此在这个个体存在物的生存活动上。既然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个体存在物,那么当我们问此在是谁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带出人称代词:我就是这个此在,此在是我,我是此在。然而,说此在是能够“去存在”具有“向来我属性”的个体存在物,这不过是提示此在的存在论机制,如前所述,此在的存在论机制始终对它蔽而不露,所以“此在为谁这个问题不仅在存在论上是个问题,而且在存在者层次上也还蔽而不露”。[7]当此在说“我”的时候,总是与他人相区别而论的,然而此在与他人的区别却是可疑的。此在落后于他人总要赶上去奋起直追,此在优越于他人则要压制他人保持领先,实际上他人成了此在生存的“标准”,此在则始终处在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
“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之各种日常的存在可能性。在这里,这些他人不是确定的他人。与此相反,任何一个他人都能代表这些他人。要紧的只是他人的不触目的、从作为共在的此在那里趁其不备就已接收过来的统治权。人本身属于他人之列并且巩固着他人的权力。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情形,而这样的‘他人’就是那些在日常的杂然共在中首先和通常‘在此’的人们。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谁’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8]
此在总是在说“我”,把我之外的人称为“他人”,以此来表示我与他人有别,然而“他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此在企图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实情而已。实际上我与他人无别,“此在为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此在这个“谁”不是任一具体的“谁”,而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常人”(das Man)。于是,“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9]海德格尔将此在这种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常人而存在的状态称为“沉沦”(Verfallen)。
所谓“常人”类似我们通常泛指的“大家”、“大众”或“我们”,实际上“常人是谁”经不起深究。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常人似乎到处在场,此在的存在、筹划、选择、责任……如此等等统统交由常人一并承担了,但是每当需要此在挺身而出去做决断之时,常人却总已溜走了。“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10]此在是谁之问,答曰“他人”。若问“他人”是谁,答曰“常人”,但若追问“常人”是谁,答案触目惊心,细思极恐:查无此人,从无此人。这意味着“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11]但是,倘若“常人”并无其人,那也就是说此在自己就是常人,它打着“常人”的旗号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去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欺”。以常人的方式存在让此在以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油然而生出身在家园的安全感。相反,让此在自己去存在,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充满危险的可能性的未来,它必须自己去筹划选择,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去承担自己的选择而产生的后果,由此而生起的却是茫茫然不知所措的“无家可归”(unheimlich)的情绪。所以,看起来“常人”不过是名义而已,此在和常人都是此在,甚至都不过是此在自己,以至于海德格尔称沉沦状态为此在“从自身跌入到自身”:“此在从它本身跌入它本身中,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12]然而此在自己去存在与以常人的方式去存在,亦即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别,不仅关涉到此在究竟是否本己地去存在的问题,更重要地是也关涉到此在究竟是以解蔽的方式还是以遮蔽的方式“显现”存在的问题。此在以常人为其自身等于锁闭了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除根”,亦即滞留于沉沦状态而把自己从自己的存在“切除下来”。[13]由此可见,此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作为生存论分析的问题,乃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我们把这个常人自己和本真的亦即本己掌握的自己加以区别。一作为常人自己,任何此在就涣散在常人之中了,就还得发现自身”。[14]因为常人并无其人,所以此在沉沦为常人实际上是“从自身跌入到自身”。不仅如此,此在自始就已沉沦,从来就没有以本己的方式存在过。这无异于说:此在从来不是它自身。倘若如此,何来此在自身?此在又如何能够发现自身?
我们不要把此在的本己存在与常人此在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两个东西。“本真的自己存在并不依栖于主体从常人那里解脱出来的那样一种例外情况;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15]这话显得十分费解:难道不应该说常人是此在本真的自己存在的一种“生存变式”?海德格尔后来的确这么说了:“当时曾显示(这里的‘当时’指的就是回答‘此在为谁’的问题之时——引者),此在首先与通常不是它自身,它倒失落于常人自身,常人自身是本真自身的一种生存上的变式”。[16]究竟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生存变式,还是常人自身是本真自身的生存上的变式?或许本就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其实都是“能在”(SeinkÖnnen)的变式。此在“去存在”乃为“能在”,即便此在逃避自己的存在而以常人的方式沉沦在世,也是因为它“能”沉沦,世间万物只有此在能够自我“除根”。所以,并非此在原本是本己的存在,后来堕落而以常人的方式沉沦,然后再去“发现自身”,回到本己的自己存在。并没有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本真的自己有待此在去发现,关键在于此在如何发现自己是“能在”。
此在之沉沦是“从自身跌入自身”,如何才能让此在“从自身回到自身”?
三、“将来”:让自身来到自身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将此在日常生活之生存活动的整体性规定为“操心”(Sorge):“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之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17]亦即生存、实际性和沉沦。在此在生存活动的整体性中,“此在之先行于自身的存在”(das Sich-vorweg-sein des Daseins)是其核心,它体现的是此在“去存在”之“能在”。
此在是“去存在”的“能在”的存在物,由此而理解“先行于自身”似乎并不困难,此在的生存即是筹划(Entwurf),因而此在始终在“开抛”之中,[18]每一次筹划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去存在。不过,“先行于自身”中的“自身”仍然疑问重重。如果说此在的存在总是“先行于自身”的,这显然并不是说此在有一个现成的自身,然后它的存在先行于这个自身,实际上“先行于自身”意味着此在没有现成的自身,不如说“自身先行”,或如萨特的发挥,“生存先于本质”,此在总有一个未来的自身有待实现。然而,这样来理解“先行于自身”的“自身”似乎仍然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所以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批评萨特把一个形而上学命题(本质先于生存)颠倒过来,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19]
然而,如果“先行于自身”意味着“自身先行”,那么这个先行的“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自身”?此在之自身在“畏”这种最极端的情绪中“现身”,畏启示着无,此为“无何有之乡”(nirgends)。在畏的情绪中,此在被嵌入无之中而个体化为自身,它被迫意识到:“我在,且不得不能在”。所以,此在之先行的自身乃为“能在”。然而,此在拒绝直面虚无,拒绝直面自己的能在,所以它不让畏的情绪浮现。若要此在直面自己的能在,唯有“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才能迫使此在直面其自身。由此,《存在与时间》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死亡观。
流俗的死亡观逃避死亡,它把死亡看作是“存在到头”: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所以死亡是发生在人生之外的事件。生存论的死亡观则把死亡看作是自始就嵌入人生之中的一种特殊的可能性,由此而“打通”了生死:死像生一样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20]
“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此在在这种可能性中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旨。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在世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在如此悬临于自身之际,此在之中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被解除了。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同时就是最极端的可能性。此在这种能在超不过死亡这种可能性。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超不过的可能性”。[21]
因此,此在直面死亡,直面的是自己之纯然可能性的能在,死亡的不可替代性使它对常人的依赖变得毫无意义,由此而使此在从沉沦状态回到了自己的能在。
然而,虽然此在之“去存在”“先行于自身”,但是它已经被抛地在世并且自始就以常人的方式而沉沦。既然此在自始就已沉沦,那么此在怎么才能确定沉沦在世的自己不是自己,向死而在,在畏中直面虚无那种无家可归的情绪中现身的自己才是本真的自己?在常人世界中没有众醉独醒者,哲学家也不例外,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唯有此在自己能够唤醒自己,这就是“良知”(Gewissen)的呼声。良知的呼声实际上无声,但此处无声胜有声,“呼声由远及远,唯欲回归者闻之”。[22]“呼声跨越了常人以及公众解释此在的讲法,这绝不意味着呼声不也一同及于常人。恰恰是在这种跨越中,呼声将那热衷于公众声誉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但那在呼唤中被剥去了栖所和遮蔽的自身却通过呼声被带回其本身”。于是,“因为被召唤的、被带来听呼声的是常人自身的那个自身,所以,常人就崩塌了”。[23]因此,是此在自己唤醒了自己:“呼唤者是此在,是在被抛境况(已经在……之中)为其能在而畏的此在。被召唤者是同一个此在,是向其最本己的能在(领先于自己)被唤起的此在。而由于从沉沦于常人(已经寓于所操劳的世界)的状态被召唤出来,此在被唤起了”。[24]
所以,此在“先行于自身”中的“自身”与先行的自身,或可理解为此在的常人自身和本己的自身,“从自身跌入自身”与“从自身回归自身”,都是此在的自身,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根源于此在“去存在”的“能在”,即是说,此在自身就是可能性,而此在之整体能在就体现在此在的时间性结构之中。通常的时间观把时间看作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线性的均匀的无限绵延,这种时间观看起来以“现在”为核心:我们以“现在”为焦点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然而实际上是以“过去”为核心的:“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推动着“将来”,所有一切都在过去被决定了。形而上学即是这样的时间观,例如黑格尔把宇宙的演化看作是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自我实现的“圆圈”,现实不过是潜在的充分展开而已。生存论的时间观则是以“将来”(Zukunft)为其核心。
通常时间观中的“将来”指的是无限的“去远”,而生存论时间观中的“将来”作为“有终的将来”却表现为“切近”。在操心的三重结构——生存、被抛和沉沦——中,对应的时间性是“将来”(先行于)、“曾在”(已经在)和“当前”(寓于),而“先行于自身”作为时间性的“将来”不是“去远”而是“切近”,亦即“让自身来到自身”:“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25]“别具一格的可能性”即死亡,此在向死而在亦即“向可能性而在”,这不是迷失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之中,而是将可能性“收回”到自身“来”,“让自身来到自身”,此即“有终的将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可以看作是关于此在自身问题的答案:
“此在根本就能够在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来到自身,并在这样让自身来到自身之际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保持住,也就是说,此在根本就生存着。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如果说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属于此在的存在,那么,就这里所揭示的及下面将进一步加以规定的意义上讲,这一向死存在只有作为将来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将来’在这里不是指一种尚未变成‘现实’的,而到某时才将是‘现实’的现在,而是指此在借以在最本己的能在中来到自身的那个‘来’.‘先行’使此在本真地是将来的,其情况是:只有当此在作为存在者层次上的此在根本总已向着自身到来,亦即在其存在中根本是将来的,先行本身才成为可能”。[26]
此在“先行于自身”亦即在“先行到死”中“先行而为可能性”,让可能性的自身来到自身,存在在此在的可能性之自身中显现。因此,此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亦即此在与存在的关系,存在在此在这里“个体化”了,在此在的“去存在”中体现为“可能性”。因而始终保持自身为可能性,便是此在的本己存在,此在的这个“自身”并非逻辑上在先的本质,而是时间上在先的“将来”——在这里“时间上在先”不是指“过去”,而是指“将来”。“将来”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先的。
我们可以把《存在与时间》看作一次宏大的“思想实验”。一切存在物皆因存在而在,但是所有存在物以某种确定性的本质为其自身,所以存在隐而不显,唯独此在这种个体存在物以存在为其自身,它体现在“去存在”之中。海德格尔试图证明最普遍的存在能够也只能通过此在这个个体存在物而显现,然而仅就《存在与时间》没有完成,海德格尔思想发生了转向而论,这场思想实验显然以失败而告终。《存在与时间》为什么没有完成?解答存在问题的此在之路因何而断绝?原因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2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在以存在为其自身,但是即便此在本真地生存,将自身视为可能性,而它所显现的仍然是此在的存在自身,而非存在自身,换言之,存在一旦成为此在的自身,存在就不再是存在自身了。
海德格尔彻底改变了追问存在问题的方式,把存在问题落实在此在这个个体性的存在物之上,这意味着最普遍的存在是以最个别化的方式显现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海德格尔貌似没有追随者,问题始终存在。
张志伟,性爱电影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


